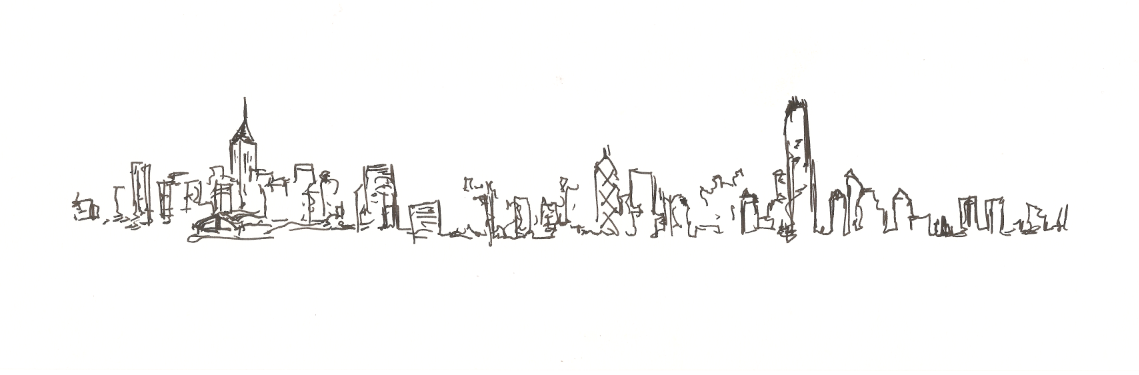從前我一直都說不準陳冠中的形象。最早
他是全華文世界第一個寫專書介紹新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的冷門作者,後來創辦《號外》引領城市文化風潮,再後來他寫電影劇本、管理唱片公司……你實在不知道
該用哪一套習見的角色去定位這個人。就像我的舊上司梁濃剛,一方面研究拉康,另一方面在電視台任職高層。也許那一代香港文化人就是這樣,見多識廣,遊歷豐
富,但卻不太張揚,無論幹了多少也許很值得稱道的功業,最後都總是好像甚麼事都沒有發生過一樣。
但自從陳冠中定居北京之 後,我們對他的印象反而清晰了。原來他始終是個作家,一個銳利的作家。幾年前,他開始有系統地書寫香港,其自省之深足令不少他的同代人汗顏,開啟了香港集 體反思的精神運動。現在,他以城市觀察者的身分,終於交出第一部談論中國大陸的小說。無論你喜不喜歡,贊同或不贊同《盛世》裏的未來願景,你都不能否認它 的確看得人冷汗直流。誰也猜不到這麼多年之後,竟是一個香港人率先寫出中國版的《美麗新世界》。
我在北京和陳冠中聊他的新書,但不免還是要從香港說起,譬如說香港文化感性中那股獨特的「冷」。
梁︰ 梁文道
陳︰ 陳冠中
梁︰ 不知道為甚麼香港的sensibility會這麼cool?
陳︰ Cool的確是最貼切的字,香港不喜歡sentimental,不喜歡濫情。
梁︰ 譬如說進念那種劇場,台灣不會有,大陸也不會有。香港很多artist,做installation和行為藝術做了這麼多年,但是從來沒有好像大陸這樣一做就沸沸揚揚,就讓人覺得厲害,覺得是世界第一。這到底是為甚麼呢?
陳 ︰ 而且就算是很重的一個題材,也要做得輕一點,也要將那個主題說得小一點。我覺那真是某個階段的西方品味,譬如說五、六十年代歐洲那種存在主義的品味,或者 是後來結構主義與美國的counter culture品味,是cool的,是冷調一些的,就是不喜歡說一些激情大主題,不喜歡激情到連自己也感動。起碼我自己就是,整天都想用最簡約的方式去說 很多事情。
梁︰ 昨天在我一本書的朗讀會中,一位讀者就選了一篇我寫的東西來讀。但我自己其實不太喜歡那篇東西,因為當時我的寫作策略是在西藏問題鬧得最激烈的時候,特地用很溫情的東西去說服一些憤青。我非常不喜歡這種方式,因為它根本不像我,可是有些讀者卻很喜歡,很奇怪。
陳︰ 大陸的官方論述也永遠是華麗的,帶感情的,句子和用字都很講究,就算是中央台的晚會,那些主持人出來說的話都是漂亮的。其實那都是套句,陳腔濫調。這可能是一個訓練。即便台灣,比起香港也多了很多感情,香港是特意將感情元素削減了。
梁︰ 台灣很強調一種很溫暖、很sweet的東西。譬如他們的唱片,那些印有歌詞的小書根本是放不進去CD盒,因為它太厚了,每一頁都要有歌者在上面用手寫下自己在錄這首歌時的心情如何如何,我們香港人看了就會說,有沒有搞錯。
陳︰ 香港的作家多半也比較cool,由劉以鬯到西西皆如是。就算西西有點童真,有點樸素;或者後來的黃碧雲比較「激」,但就是沒有那種溫情。
梁︰ 所以在這兩者之間,香港才有了一個特別的文化的感性存在。這種感性很世故,乃至於我們的電影沒有很多溫情戲,寧願喜歡「笑爆咀」,苦中即時求樂。
陳 ︰ 我們在很小的時候已很害怕,不是怕,而是已經開始會去嘲諷「文藝腔」,去拒絕這種東西。起碼我自己成長、寫作的時候,就很害怕給人說是「文藝腔」。於是這 個「文藝腔」的傳統就在香港被切斷了。我們又怕被人認為是「扮嘢」,寧願「存真」也不要「扮嘢」,總之就是不想世界太浪漫,我們對浪漫本身就有疑問,香港 人並不浪漫。我們更不喜歡那些自怨自艾,然後覺得自己很悲慘的情感,譬如說台灣的「悲情」和大陸的「百年國恥」。
梁 ︰ 所以當台灣一份刊物叫我寫四九年的香港時,我才發現香港相當有趣,很多人從來沒有覺得自己很慘很失敗,我們在香港住了這麼久,你何時聽過香港人會這樣說? 所以龍應台那本書,就只有台灣人才寫得出來。你父母那一代從上海逃來香港,他們會不會常常這樣喊苦?沒有呀。我認識很多人都是由大陸下來,而且當年還真 苦。但問題就是他們從來不講,也從來不會拿這些事來說,更不會將這件事變作一種cultural element。
陳︰我父母那一代都好像 沒有太強調那種苦。他們不會當自己是一個受害者,整天圍繞受害者這個主題,然後一直覺得自己的人生怎麼會這樣苦。我們很快就可以轉換心境。我記得小時候他 們有講過香港是一個福地,說香港真的很好。他們都有一個比較的想法,起碼與在大陸的朋友和親戚的遭遇不同,他們都向前看,很樂觀,然後急急要「搵食」。
但自從陳冠中定居北京之 後,我們對他的印象反而清晰了。原來他始終是個作家,一個銳利的作家。幾年前,他開始有系統地書寫香港,其自省之深足令不少他的同代人汗顏,開啟了香港集 體反思的精神運動。現在,他以城市觀察者的身分,終於交出第一部談論中國大陸的小說。無論你喜不喜歡,贊同或不贊同《盛世》裏的未來願景,你都不能否認它 的確看得人冷汗直流。誰也猜不到這麼多年之後,竟是一個香港人率先寫出中國版的《美麗新世界》。
我在北京和陳冠中聊他的新書,但不免還是要從香港說起,譬如說香港文化感性中那股獨特的「冷」。
梁︰ 梁文道
陳︰ 陳冠中
梁︰ 不知道為甚麼香港的sensibility會這麼cool?
陳︰ Cool的確是最貼切的字,香港不喜歡sentimental,不喜歡濫情。
梁︰ 譬如說進念那種劇場,台灣不會有,大陸也不會有。香港很多artist,做installation和行為藝術做了這麼多年,但是從來沒有好像大陸這樣一做就沸沸揚揚,就讓人覺得厲害,覺得是世界第一。這到底是為甚麼呢?
陳 ︰ 而且就算是很重的一個題材,也要做得輕一點,也要將那個主題說得小一點。我覺那真是某個階段的西方品味,譬如說五、六十年代歐洲那種存在主義的品味,或者 是後來結構主義與美國的counter culture品味,是cool的,是冷調一些的,就是不喜歡說一些激情大主題,不喜歡激情到連自己也感動。起碼我自己就是,整天都想用最簡約的方式去說 很多事情。
梁︰ 昨天在我一本書的朗讀會中,一位讀者就選了一篇我寫的東西來讀。但我自己其實不太喜歡那篇東西,因為當時我的寫作策略是在西藏問題鬧得最激烈的時候,特地用很溫情的東西去說服一些憤青。我非常不喜歡這種方式,因為它根本不像我,可是有些讀者卻很喜歡,很奇怪。
陳︰ 大陸的官方論述也永遠是華麗的,帶感情的,句子和用字都很講究,就算是中央台的晚會,那些主持人出來說的話都是漂亮的。其實那都是套句,陳腔濫調。這可能是一個訓練。即便台灣,比起香港也多了很多感情,香港是特意將感情元素削減了。
梁︰ 台灣很強調一種很溫暖、很sweet的東西。譬如他們的唱片,那些印有歌詞的小書根本是放不進去CD盒,因為它太厚了,每一頁都要有歌者在上面用手寫下自己在錄這首歌時的心情如何如何,我們香港人看了就會說,有沒有搞錯。
陳︰ 香港的作家多半也比較cool,由劉以鬯到西西皆如是。就算西西有點童真,有點樸素;或者後來的黃碧雲比較「激」,但就是沒有那種溫情。
梁︰ 所以在這兩者之間,香港才有了一個特別的文化的感性存在。這種感性很世故,乃至於我們的電影沒有很多溫情戲,寧願喜歡「笑爆咀」,苦中即時求樂。
陳 ︰ 我們在很小的時候已很害怕,不是怕,而是已經開始會去嘲諷「文藝腔」,去拒絕這種東西。起碼我自己成長、寫作的時候,就很害怕給人說是「文藝腔」。於是這 個「文藝腔」的傳統就在香港被切斷了。我們又怕被人認為是「扮嘢」,寧願「存真」也不要「扮嘢」,總之就是不想世界太浪漫,我們對浪漫本身就有疑問,香港 人並不浪漫。我們更不喜歡那些自怨自艾,然後覺得自己很悲慘的情感,譬如說台灣的「悲情」和大陸的「百年國恥」。
梁 ︰ 所以當台灣一份刊物叫我寫四九年的香港時,我才發現香港相當有趣,很多人從來沒有覺得自己很慘很失敗,我們在香港住了這麼久,你何時聽過香港人會這樣說? 所以龍應台那本書,就只有台灣人才寫得出來。你父母那一代從上海逃來香港,他們會不會常常這樣喊苦?沒有呀。我認識很多人都是由大陸下來,而且當年還真 苦。但問題就是他們從來不講,也從來不會拿這些事來說,更不會將這件事變作一種cultural element。
陳︰我父母那一代都好像 沒有太強調那種苦。他們不會當自己是一個受害者,整天圍繞受害者這個主題,然後一直覺得自己的人生怎麼會這樣苦。我們很快就可以轉換心境。我記得小時候他 們有講過香港是一個福地,說香港真的很好。他們都有一個比較的想法,起碼與在大陸的朋友和親戚的遭遇不同,他們都向前看,很樂觀,然後急急要「搵食」。